南帆:文學(xué)批評(píng)拿什么對(duì)“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+”發(fā)聲?

何 平
主持人語
本組筆談開欄之時(shí),南帆教授即以《博弈場(chǎng)中的文學(xué)視角》從文學(xué)傳統(tǒng)和文學(xué)話語與諸話語之關(guān)系的角度拓展我們討論的疆界。此番《文學(xué)知識(shí)、歷史與欲望》另開一局。兩文對(duì)讀,意味深長(zhǎng),后文切實(shí)地質(zhì)疑和對(duì)話著前文。我尊敬這種自我反思的精神和態(tài)度。
對(duì)于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,學(xué)院批評(píng)界早有回應(yīng),比如歐陽友權(quán)、黃鳴奮、邵燕君、夏烈等,我也在七八年之前讀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、談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,但這種談?wù)撈窕具€囿于一個(gè)小圈子。南帆教授此文可以讓我們檢討五四新文學(xué)以來所建立起來的“文學(xué)知識(shí)”以及這套“文學(xué)知識(shí)”體系對(duì)當(dāng)下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的“不適應(yīng)癥”。按照他的觀察,“為人生”的文學(xué)和“脫離人生”的文學(xué)、文學(xué)的歷史邏輯和欲望邏輯并不能彼此收編和兼容。那么問題就來了:我們當(dāng)下的批評(píng)家們?nèi)绻€因襲既有知識(shí)闡釋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,只能是各說各話。退一步講,如果我們堅(jiān)守著傳統(tǒng)印刷媒體時(shí)代的文學(xué)知識(shí)和傳統(tǒng),殘山剩水能不能守得住?南帆教授提出的問題值得思考,是不是我們今天的文學(xué),并不是傳統(tǒng)文學(xué)與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相安無事,而是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的登場(chǎng),已經(jīng)使得整個(gè)文學(xué)生態(tài)成了“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+”?如果我們的文學(xué)批評(píng)還要對(duì)當(dāng)下文學(xué)發(fā)聲,那么當(dāng)務(wù)之急可能是以今天之文學(xué)審視我們已成慣例之“文學(xué)知識(shí)”。“新”文學(xué)已經(jīng)確實(shí)的浮出水面。期待此文成為另一個(gè)起點(diǎn),讓我們以更遼闊的心態(tài)觀察和接納我們時(shí)代的“各種”文學(xué),進(jìn)而重新想象“文學(xué)”和“文學(xué)本體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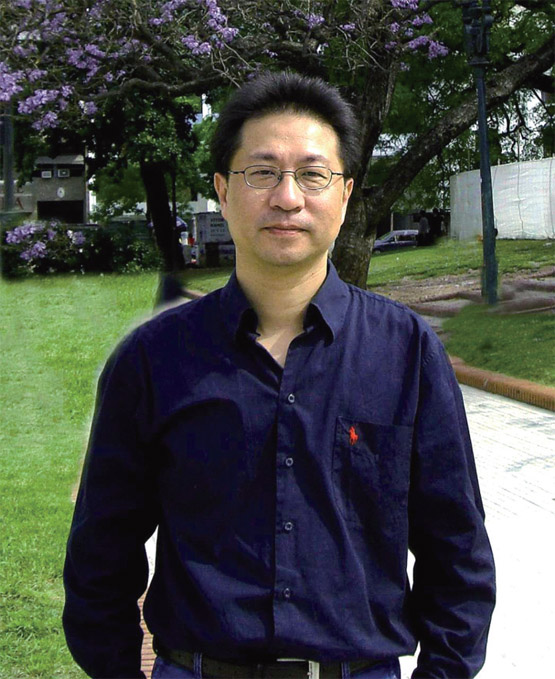
南 帆
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巨大的市場(chǎng)號(hào)召力再度證明了通俗文學(xué)的半壁江山,那么,作為某種理論回應(yīng),“欲望”有必要納入文學(xué)知識(shí)成為一個(gè)常規(guī)范疇,并且與“無意識(shí)”、“象征性補(bǔ)償”等另一些精神分析的概念相互補(bǔ)充。
現(xiàn)今,兩種文學(xué)類型的分歧、競(jìng)爭(zhēng)比以往任何時(shí)代都要尖銳。對(duì)于文學(xué)想象說來,遵從歷史邏輯與遵從欲望邏輯包含了內(nèi)在的對(duì)立,批評(píng)必須為兩種類型的文學(xué)解讀設(shè)置不同的代碼系統(tǒng)。
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制造的文學(xué)震蕩正在持續(xù),諸多人們熟悉的文學(xué)命題無不察覺到這個(gè)龐然大物的壓力。現(xiàn)今的文學(xué)知識(shí)體系大約擁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。20世紀(jì)之初,五四新文化啟動(dòng)的“文學(xué)革命”曾經(jīng)帶來文學(xué)知識(shí)的深刻重組。傳統(tǒng)的考據(jù)、義理、詞章迅速地被“文學(xué)概論”覆蓋,新型的文學(xué)教育得到了學(xué)院體制的保駕護(hù)航。盡管某些前沿的論題——例如現(xiàn)代主義或者超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——仍然存在種種爭(zhēng)議,但是,多數(shù)人業(yè)已就文學(xué)的形態(tài)、功能、類型、符號(hào)體系、傳播網(wǎng)絡(luò)、經(jīng)典篇目等達(dá)成廣泛共識(shí)。如果說,古典文學(xué)轉(zhuǎn)換為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曾經(jīng)出現(xiàn)巨大的顛簸,那么,20世紀(jì)的文學(xué)知識(shí)業(yè)已再度穩(wěn)定了如下的標(biāo)準(zhǔn):何謂文學(xué),何謂好的文學(xué)。
盡管這種標(biāo)準(zhǔn)迄今仍然在印刷文學(xué)之中享有崇高的聲望,但是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仿佛帶來了另一個(gè)文化空間。互聯(lián)網(wǎng)上360百科的“小說”條目之中,《紅樓夢(mèng)》《阿Q正傳》或者《安娜·卡列寧娜》《追憶逝水華年》已經(jīng)不再充當(dāng)小說的經(jīng)典范本;條目推薦的小說標(biāo)本多半流行于互聯(lián)網(wǎng),例如《傾盡天下》《重生之帝妃謀》《絕色傾城》《悲傷逆流成河》等等。相對(duì)于印刷文學(xué)的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、現(xiàn)代主義乃至魔幻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提供了種種前所未有的類型,諸如玄幻小說、冶艷小說、穿越小說、網(wǎng)游小說,或者架空歷史小說、耽美小說、末日生存小說。
當(dāng)然,矜持的學(xué)院并不急于表態(tài),大多數(shù)文學(xué)教授毋寧說置若罔聞。然而,當(dāng)社會(huì)的閱讀重心從印刷傳媒轉(zhuǎn)向互聯(lián)網(wǎng)之后,如火如荼的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必然謀求文學(xué)殿堂的正統(tǒng)身份。除了擁有不可比擬的讀者數(shù)量,互聯(lián)網(wǎng)同時(shí)展示了一個(gè)新型的知識(shí)傳播體系。對(duì)于門戶儼然的學(xué)院來說,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沖擊可能迅速顛覆沿襲已久的教學(xué)體系。這個(gè)意義上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的積累和總結(jié)不僅促進(jìn)了文學(xué)知識(shí)的持續(xù)增長(zhǎng),更重要的是逐漸顯示出兩套文學(xué)知識(shí)的分歧和角逐。
“為人生”的文學(xué)與批評(píng)
“詩言志”或者“文以載道”是古代批評(píng)家反復(fù)陳述的信條。五四新文學(xué)運(yùn)動(dòng)之后,“為人生”的口號(hào)成為文學(xué)的最強(qiáng)音。作為這個(gè)口號(hào)的呼應(yīng),社會(huì)歷史批評(píng)學(xué)派急速崛起。古老的神話傳奇、宗經(jīng)征圣退出了理論舞臺(tái),“歷史”成為舉足輕重的范疇。馬克思主義批評(píng)家不僅將所謂的“志”、“道”、“人生”納入社會(huì)歷史;同時(shí),物質(zhì)決定精神、經(jīng)濟(jì)基礎(chǔ)決定上層建筑構(gòu)成了他們剖析社會(huì)歷史結(jié)構(gòu)的基本原則。根據(jù)社會(huì)歷史的語境考察文學(xué)的產(chǎn)生及其功能,并且在文學(xué)的解讀之中捕獲社會(huì)歷史演變的種種信息,這種認(rèn)識(shí)方式已經(jīng)成為眾多文學(xué)知識(shí)的前提。學(xué)院的文學(xué)教育表明,文學(xué)理論的諸多命題無不成為這種前提的擴(kuò)展和延伸。同時(shí),這種前提形成的鑒別與衡量決定了作家的文學(xué)史位置,例如魯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構(gòu)成的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第一方陣。
許多批評(píng)家心目中,“為人生”的文學(xué)亦即“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”文學(xué)。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文學(xué)再現(xiàn)了社會(huì)的世俗百態(tài),再現(xiàn)了形形色色的“人生”故事,正視大眾的疾苦,關(guān)注小人物命運(yùn)。但是,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文學(xué)所謂的“現(xiàn)實(shí)”并非一張即時(shí)性的平面圖,一種沒有深度的表象堆砌;“現(xiàn)實(shí)”包含了昨天、今天、明天之間必然的歷史脈絡(luò),包含了現(xiàn)實(shí)之所以如此的原因。這種歷史脈絡(luò)可以解釋文學(xué)人物的性格形成,解釋他們命運(yùn)之中的悲喜劇,同時(shí)解釋他們置身的“典型環(huán)境”如何延續(xù)到讀者的“人生”之中,從而喚起批判、反抗與革命的信念與激情。所以,盡管賈寶玉、阿Q、安娜存活于另一個(gè)世界,但是,沒有人覺得他們的悲歡“干卿何事”,“歷史”將文學(xué)中的“人生”與此刻身邊的社會(huì)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
20世紀(jì)20年代,“為人生”的文學(xué)口號(hào)來自文學(xué)研究會(huì)。這個(gè)文學(xué)社團(tuán)的眾多作家不僅鄙視“唯美派”的風(fēng)花雪月,同時(shí)對(duì)《禮拜六》《游戲雜志》以及鴛鴦蝴蝶派之類通俗文學(xué)表示不屑。才子佳人、黑幕大觀、武俠偵探、宮闈秘聞,諸如此類的消遣性故事消磨斗志、麻醉精神,不啻于戕害大眾的文化毒品。相當(dāng)長(zhǎng)的一段時(shí)間,所謂的通俗文學(xué)成了文學(xué)知識(shí)的否棄對(duì)象。大部分文學(xué)史教科書與學(xué)院的課堂拒絕研究,甚至拒絕談?wù)摗Mǔ#@些作品遭受拒絕的首要理由是脫離現(xiàn)實(shí)的“人生”。一幫無聊文人杜撰各種離奇的情節(jié),編織催情白日夢(mèng),驚險(xiǎn)的生離死別或者揪心的懸念背后不存在真實(shí)的氣息;一些等而下之的粗劣之作甚至形同文字垃圾。
“欲望”與“現(xiàn)實(shí)”
然而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的洶涌大潮沖垮了文學(xué)知識(shí)構(gòu)筑的脆弱堤壩。如果說,瓊瑤、金庸、梁羽生們扮演了復(fù)興通俗文學(xué)的先鋒,那么,后續(xù)的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終于蔚為大觀。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對(duì)于社會(huì)歷史批評(píng)學(xué)派所圍繞的“歷史”范疇無動(dòng)于衷。從眾多武俠共同追逐一本武林秘籍到一幢兇宅突如其來地閃現(xiàn)吸血鬼,從若干后宮妃子密謀爭(zhēng)寵到幾個(gè)純潔的青春期少女為夢(mèng)幻之中的白馬王子灑下一掬晶瑩的淚珠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制造的懸疑、驚悚、爭(zhēng)風(fēng)吃醋和秘密懷春的確僅僅是一些短暫的臨時(shí)性情緒波動(dòng)。人們無法從中發(fā)現(xiàn)支配歷史的深刻沖動(dòng)。描述歷史內(nèi)部構(gòu)造的眾多范疇無助于解釋這些故事,例如政治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,或者種族、階級(jí)、性別、國(guó)家等等。盡管巧妙的懸念設(shè)置令人欲罷不能,奇幻的場(chǎng)面一個(gè)接一個(gè)拋出來,但是,這些眼花繚亂的故事與讀者的生活沒有內(nèi)在的精神銜接。無論是就業(yè)、購(gòu)房、婚姻還是縮小城鄉(xiāng)差別、改善醫(yī)患關(guān)系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無法提供任何值得信任的參考。
盡管如此,一個(gè)不爭(zhēng)的事實(shí)是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擁有龐大的讀者群。人們不得不面對(duì)一個(gè)令人費(fèi)解的后續(xù)問題:脫離現(xiàn)實(shí)“人生”的作品為什么竟然贏下了如此之大的市場(chǎng)? 許多時(shí)候,人們可以聽到了大量“質(zhì)樸”的回應(yīng)。一個(gè)會(huì)計(jì)剛剛從眾多財(cái)務(wù)報(bào)表之間脫身,一個(gè)溫習(xí)功課的考生打算松弛一下緊張的精神,一個(gè)廚師試圖離開煙火繚繞的廚房休息半小時(shí)——什么是他們合適的文學(xué)讀物?這時(shí),《誅仙》顯然比曹雪芹和普魯斯特有趣。等待一趟晚點(diǎn)的航班或者必須在嘈雜的地鐵車廂度過大半個(gè)小時(shí),多少人愿意琢磨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或者福樓拜的《一顆純樸的心》?對(duì)大多數(shù)讀者來說,娛樂是他們的首選。他們甚至坦率地表示,恰恰因?yàn)榫蜆I(yè)、購(gòu)房或者開拓發(fā)展空間如此渺茫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至少有助于暫時(shí)遺忘各種挫折帶來的不快。當(dāng)會(huì)計(jì)、考生、廚師納入“大眾”范疇并且擁有市場(chǎng)消費(fèi)者的身份之后,他們的愿望必將迅速轉(zhuǎn)換為文學(xué)的生產(chǎn)訂單。必須承認(rèn),這種狀況是對(duì)文學(xué)教授的嚴(yán)重挑戰(zhàn),文學(xué)的意義、功能不得不重新規(guī)劃和描述。有人感嘆地說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繞過了五四新文學(xué)而徑直匯合到鴛鴦蝴蝶派,這個(gè)事實(shí)甚至令人懷疑20世紀(jì)的文學(xué)教育成效。
在我看來,考察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與現(xiàn)實(shí)“人生”的聯(lián)系,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到了正視一個(gè)概念的時(shí)候:相對(duì)于人們不斷重復(fù)的“歷史”范疇,“欲望”是某些文學(xué)介入讀者精神生活的另一種形式。由于精神分析學(xué)的洗禮,人們對(duì)于“欲望”并不陌生。許多時(shí)候,某些不合時(shí)宜的欲望將會(huì)遭到社會(huì)規(guī)則的抑制和封閉,欲望的撲空通常意味了主體的某種現(xiàn)實(shí)匱乏。精神分析學(xué)認(rèn)為,受挫的欲望并未消失,而是潛伏于無意識(shí)的某個(gè)角落,等待理性監(jiān)控松懈之際乘隙逸出。逸出的欲望時(shí)常喬裝打扮,借助各種符號(hào)和意象從事象征性表演。許多人時(shí)常虛構(gòu)一段情節(jié)補(bǔ)償現(xiàn)實(shí)匱乏,例如膽怯者幻想自己擁有絕世武功,姿色平庸者幻想自己的花容月貌。這時(shí),欲望帶動(dòng)的想象已經(jīng)與文學(xué)很接近了。事實(shí)上,弗洛伊德即是按照這種邏輯描述文學(xué)。他將文學(xué)形容為“白日夢(mèng)”,其核心觀點(diǎn)是:未曾滿足的欲望成為想象的催化劑。
受挫欲望的象征性補(bǔ)償機(jī)制很大程度地解釋了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取悅大眾的秘密。武俠和驚險(xiǎn)小說隱含了英雄夢(mèng)和淋漓盡致的復(fù)仇,后妃們勾心斗角贏下的是帝王的愛情和榮華富貴,青春美少女保存了濾盡煙火氣息的純情,穿越小說可以拋開世俗的煩惱遁入另一個(gè)快樂的空間。當(dāng)代故事之中,“總裁”和“女上司”是炙手可熱的主角,他/她們的瀟灑、精致、霸道以及令人垂涎的緋聞無不隱含了腰纏萬貫的前提。總之,權(quán)勢(shì)、財(cái)富、性和情場(chǎng)上的贏家、暴力對(duì)抗的勝利者——這些誘人的情節(jié)背后隱藏了現(xiàn)實(shí)中遙不可及的榮耀和快感。換句話說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并未脫離現(xiàn)實(shí)“人生”,而是以文學(xué)想象集中表征一個(gè)特殊的“人生”主題:受挫欲望的補(bǔ)償。相對(duì)于日常工作的理性狀態(tài),人們的業(yè)余娛樂往往交付無意識(shí)掌控。這時(shí),遭受壓抑的欲望蠢蠢欲動(dòng),繼而與等待多時(shí)的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一拍即合。當(dāng)然,精神分析學(xué)的“欲望”及其后續(xù)故事僅僅是一種心理圖式,而不是歷史結(jié)構(gòu)。盡管“欲望”帶來心理“共振”的強(qiáng)烈程度可能超出文學(xué)顯現(xiàn)的“歷史”動(dòng)向,但是,沒有嵌入歷史結(jié)構(gòu)的心理圖式不可能改造歷史,現(xiàn)實(shí)匱乏的虛擬補(bǔ)償不可能消除匱乏的產(chǎn)生原因。
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與傳統(tǒng)文學(xué)的分歧、競(jìng)爭(zhēng)
如果說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巨大的市場(chǎng)號(hào)召力再度證明了通俗文學(xué)的半壁江山,那么,作為某種理論回應(yīng),“欲望”有必要納入文學(xué)知識(shí)成為一個(gè)常規(guī)范疇,并且與“無意識(shí)”、“象征性補(bǔ)償”等另一些精神分析的概念相互補(bǔ)充。當(dāng)然,提出“歷史”與“欲望”兩個(gè)考察文學(xué)的范疇,并非一分為二地重新分配另一些概念的歸宿,例如精英與大眾、官方與民間、經(jīng)典與市場(chǎng)、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與印刷文學(xué),如此等等。事實(shí)上,介入文學(xué)場(chǎng)域的諸多因素往往按照不同的比例形成各種組合。同時(shí),“歷史”與“欲望”并沒有成為兩種迥然不同的純粹模式,彼此絕緣。首先,所謂的通俗文學(xué)并非一個(gè)“本質(zhì)主義”的概念,文學(xué)史的軸線上,某些通俗文學(xué)——譬如詞、曲、話本——曾經(jīng)在另一個(gè)時(shí)代轉(zhuǎn)換為經(jīng)典文學(xué);其次,許多通俗文學(xué)并未拒絕“歷史”信息,例如金庸武俠小說之中明史與清史的背景;另一方面,“為人生”的文學(xué)并不意味著“欲望”的徹底清除,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史上那一批“革命加戀愛”的小說甚至流露出縱欲的氣息。
然而,不論二者之間存在多少交集,這個(gè)判斷的意義并未縮減:現(xiàn)今,兩種文學(xué)類型的分歧、競(jìng)爭(zhēng)比以往任何時(shí)代都要尖銳。對(duì)于文學(xué)想象說來,遵從歷史邏輯與遵從欲望邏輯包含了內(nèi)在的對(duì)立,批評(píng)必須為兩種類型的文學(xué)解讀設(shè)置不同的代碼系統(tǒng)。一個(gè)意味深長(zhǎng)的文學(xué)史事實(shí)是,“為人生”的文學(xué)很大程度地塑造了五四時(shí)期一代青年的精神,他們借助文學(xué)洞察歷史,決定自己的命運(yùn);相形之下,現(xiàn)今許多年輕讀者的心目中,文學(xué)僅僅是一種娛樂,一種失意之際的慰藉,一種欲望的想象性完成——總之,與他們置身的生活僅有微弱的心理聯(lián)系。當(dāng)然,這個(gè)事實(shí)本身即是深刻的歷史產(chǎn)物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