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永玉的文學(xué)行當(dāng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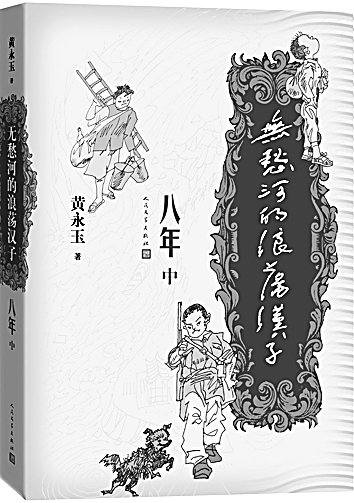
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·八年》(中) 黃永玉著 人民文學(xué)出版社
編者按
今年92歲高齡的黃永玉先生,在過(guò)往的人生中,始終用藝術(shù)的眼光發(fā)現(xiàn)生活的美,用真誠(chéng)的情懷記錄不同時(shí)代的風(fēng)土人情,足跡遍及湘西、閩南、上海、香港、北京以及世界多地。他用筆畫(huà)下走過(guò)的山山水水,也用筆寫(xiě)下所見(jiàn)的人情與風(fēng)俗。幾十年來(lái),黃永玉亦畫(huà)亦文,在繪畫(huà)中追求文學(xué)的美,在文學(xué)中追求藝術(shù)的境界。
9月28日,在黃永玉的新書(shū)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·八年》(中部)首發(fā)之際,兩位學(xué)者以“黃永玉的文學(xué)行當(dāng)”為主題,在福建泉州也即此書(shū)所涉之地進(jìn)行了一場(chǎng)精彩對(duì)談。本期讀書(shū)會(huì)特整理其中精彩內(nèi)容,以期與讀者共同感受這位文學(xué)藝術(shù)名家?guī)资瓿錆M(mǎn)正能量的創(chuàng)作之路。
嘉賓:
李輝(首屆魯迅文學(xué)獎(jiǎng)獲得者、人民日?qǐng)?bào)高級(jí)記者、作家)
張新穎(第六屆魯迅文學(xué)獎(jiǎng)獲得者、復(fù)旦大學(xué)教授、博導(dǎo))
與文學(xué)一生相伴
李輝:在許多場(chǎng)合,黃永玉先生不止一次地說(shuō),在我的行當(dāng)里面,文學(xué)排第一,雕刻排第二,繪畫(huà)排第三。只不過(guò),“黑畫(huà)”貓頭鷹、滿(mǎn)塘荷花、一枚猴票、一個(gè)酒鬼瓶,太為人熟知,文學(xué)家黃永玉的另一番風(fēng)景,則不免有些被遮掩了,所以大家對(duì)他的文學(xué)并不是很了解。
我和黃永玉1982年認(rèn)識(shí),真正來(lái)往是在1986年,到今年整整30年。
20世紀(jì)30年代起,黃永玉開(kāi)始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,并發(fā)表一些插圖。1944年在江西開(kāi)始寫(xiě)詩(shī),寫(xiě)長(zhǎng)篇連載。目前能搜集到最早的作品是在上海《詩(shī)創(chuàng)作》叢刊上發(fā)表的長(zhǎng)詩(shī)《風(fēng)車(chē)和我的瞌睡》。1948年之后,他到香港《大公報(bào)》工作,也發(fā)表各種長(zhǎng)詩(shī)。1950年,他回湘西旅行,撰寫(xiě)長(zhǎng)篇游記《火里鳳凰》,在香港《大公報(bào)》副刊連載。在擔(dān)任《大公報(bào)》副刊業(yè)余美術(shù)編輯之外,他還編寫(xiě)劇本,其中喜劇《兒女經(jīng)》被拍成電影,系以其友人唐人(《金陵春夢(mèng)》一書(shū)作者)的家庭生活為素材而創(chuàng)作的,女明星石慧因在該片的出色表演而當(dāng)選為最佳女演員。后來(lái)黃永玉又寫(xiě)了一部劇本《海上故事》,劇本已完成,在醞釀拍攝時(shí),因?qū)а葙M(fèi)穆突然病逝而夭折。
1953年,黃永玉離開(kāi)香港,定居北京,以人民日?qǐng)?bào)特約記者的身份,去了趟小興安嶺森林,并在《人民日?qǐng)?bào)》上發(fā)表了一組攝影照片,后來(lái)又陸陸續(xù)續(xù)發(fā)表相關(guān)文章,如《森林小學(xué)》《森林黃昏》等。
1964年,在“四清運(yùn)動(dòng)”期間,黃永玉開(kāi)始“動(dòng)物短句”的創(chuàng)作,每個(gè)動(dòng)物只寫(xiě)一句話,再配一幅動(dòng)物畫(huà),圖文相映成趣,互為補(bǔ)充。這些短句,似格言,非格言;似散文句式,卻又更接近于散文詩(shī)。這些文字于“文革”后結(jié)集出版,即“永玉六記”的第一本。1997年擴(kuò)展為“永玉六記”。
1970年,身在“五七干校”的黃永玉,在經(jīng)歷“文革”初期的的批斗之后,下放到“干校”勞動(dòng),與文學(xué)史上眾多優(yōu)秀作家的寫(xiě)作一樣,黃永玉以“潛在寫(xiě)作”方式創(chuàng)作長(zhǎng)詩(shī)《老婆呀!不要哭》,記二百多行。
1979年,黃永玉完成了長(zhǎng)篇散文《太陽(yáng)下的風(fēng)景》,讓他的散文寫(xiě)作一下子就達(dá)到很高的起點(diǎn)。
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可以說(shuō)是黃永玉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的又一個(gè)高峰。在20世紀(jì)40年代初,他就開(kāi)始想寫(xiě)這部小說(shuō),真正開(kāi)始寫(xiě)是1990年前后,完成十幾萬(wàn)字后一度停筆;十幾年后,于2008年再度續(xù)寫(xiě)。黃永玉創(chuàng)作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的過(guò)程,頗類(lèi)似于老舍、矛盾、巴金、沈從文等現(xiàn)代作家當(dāng)年的狀態(tài):一邊寫(xiě),一邊發(fā)表。連載這一作品的是國(guó)內(nèi)最重要的大型文學(xué)刊物之一《收獲》。到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連載第7年了,期期不落,每期都2萬(wàn)多字,以個(gè)性的文字描述他兒時(shí)的經(jīng)歷,現(xiàn)在才寫(xiě)到泉州部分,后面的還很長(zhǎng),這令我對(duì)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以后的敘述和格局充滿(mǎn)期待。
所以,整個(gè)文學(xué)是伴隨黃永玉一生的。
充滿(mǎn)能量的個(gè)性之作
張新穎:《太陽(yáng)下的風(fēng)景》以寫(xiě)黃永玉表叔沈從文為主,1979年創(chuàng)作,1980年發(fā)表。那時(shí)中國(guó)剛剛從“文革”當(dāng)中恢復(fù)出來(lái),我們的語(yǔ)言、文字形態(tài)就如同一整塊板結(jié)了的土壤一樣,沒(méi)有彈性,沒(méi)有營(yíng)養(yǎng)。這篇散文不符合常規(guī)的文章寫(xiě)法,單單從文字的字面上來(lái)講,就讓大家感到非常驚訝,更不要說(shuō)其中流露的很深厚的對(duì)家鄉(xiāng)的感情,對(duì)他表叔的感情,對(duì)湘西文化的感情。大家都覺(jué)得這篇文章好,但是又很難說(shuō)清楚它好在哪里。
一般作家創(chuàng)作的最好時(shí)期是在他的青年時(shí)代,到中年就開(kāi)始下降,到了老年就更不用說(shuō)了。而黃永玉82歲的時(shí)候還在創(chuàng)作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,最讓人敬佩的是,他的作品里面充滿(mǎn)朝氣。那生機(jī)勃勃的力量,超過(guò)了年輕人的力量。通過(guò)寫(xiě)無(wú)愁河,不斷生產(chǎn)出能量,我覺(jué)得他不僅僅把能量保存在文字里面,傳遞給讀者,他本人也從寫(xiě)作中獲得能量,很享受這樣一個(gè)行為。讀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,會(huì)給讀者帶來(lái)生命的滋養(yǎng)。一旦喜歡上它,就舍不掉。很少有這樣一部不斷給人帶來(lái)能量的作品。
李輝:20世紀(jì)50年代之后的文學(xué),強(qiáng)調(diào)大眾化的方向,小說(shuō)的主人公以工農(nóng)兵的形象為主,里面充斥著大量的政治文件和社論語(yǔ)言。那個(gè)時(shí)代的作家,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。沈從文在1949年之后,一度還是想寫(xiě)作,但是他寫(xiě)《邊城》《湘行散記》的語(yǔ)言風(fēng)格,并不符合當(dāng)時(shí)的文學(xué)要求。他一直改變,沒(méi)有成功。他想寫(xiě)英雄人物,采訪了十多年,計(jì)劃寫(xiě)篇長(zhǎng)篇小說(shuō),最后還是沒(méi)寫(xiě)出來(lái)。黃永玉1979年寫(xiě)的文章,沒(méi)有20世紀(jì)50年代以來(lái)政治抒情的痕跡,包括他在干校寫(xiě)的《老婆呀!不要哭》,完全秉承了19世紀(jì)俄羅斯詩(shī)歌的特點(diǎn)。他跟上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腳步,但又一直保持自己的語(yǔ)言風(fēng)格。《太陽(yáng)下的風(fēng)景》一發(fā)表,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關(guān)注,評(píng)價(jià)極高。黃永玉的散文語(yǔ)言不講究套路,看他的文章,有時(shí)候看著看著,就不知道寫(xiě)到哪里去了,但到最后,他又能奇跡般地收回來(lái)。沒(méi)有固定的格式,但是每一種表述,都能達(dá)到一定境界,這是他語(yǔ)言的特點(diǎn)。
隨心所欲的寫(xiě)作境界
張新穎:語(yǔ)言當(dāng)然跟人的生命狀態(tài)有關(guān),我讀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,還有一個(gè)特別大的感受就是一個(gè)人的生命寬度特別重要。在黃永玉的生命里,可以看到很野的、很文的、很粗、很成熟的這些不同的東西結(jié)合在一個(gè)生命里面,它的質(zhì)量和密度就特別大,也顯得特別豐富。
對(duì)黃永玉來(lái)說(shuō),在他成長(zhǎng)的過(guò)程當(dāng)中,沒(méi)什么是不好的,沒(méi)什么值得嫌棄,所有的東西都成為滋養(yǎng)他的東西,而且他把這些都寫(xiě)了出來(lái)。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寫(xiě)得這么長(zhǎng),就是不選擇,想怎么寫(xiě)就怎么寫(xiě)。在他看來(lái),所有的東西都是有意義的。比如一條街道,他從頭寫(xiě)到尾,一家一家鋪?zhàn)訉?xiě)過(guò)來(lái),把他能夠記得的東西都寫(xiě)下來(lái)。“生命當(dāng)中沒(méi)有任何經(jīng)驗(yàn)是沒(méi)有的,生命當(dāng)中沒(méi)有任何時(shí)間是虛度的。”這句話用在黃永玉身上特別合適。
他的寫(xiě)作,已經(jīng)達(dá)到隨心所欲的一個(gè)境界。
李輝:作家在隨心所欲的創(chuàng)作過(guò)程中,其實(shí)是靠很多東西在支撐的。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說(shuō)過(guò):“黃永玉的記性真好!”這是他成功創(chuàng)作很重要的一點(diǎn)。臧克家也談過(guò):“黃永玉口才好,記憶好,而且很幽默。”另外一個(gè),他閱讀量非常大,很多書(shū)都是我沒(méi)看過(guò)的。去年他用了將近一年的時(shí)間臨摹《清明上河圖》,主要目的是看《清明上河圖》里人物情景之間的呼應(yīng)關(guān)系。
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是從故鄉(xiāng)開(kāi)始,格局很大,同學(xué)與同學(xué)之間、朋友與朋友之間、仇人與仇人之間,都有一個(gè)呼應(yīng)關(guān)系。而且每到一個(gè)地方,不斷有新的人物出現(xiàn),很多很不起眼的小人物,他也用心在寫(xiě)。當(dāng)一個(gè)人物寫(xiě)完了之后,他發(fā)現(xiàn)很有意思,就會(huì)圍繞這個(gè)人物繼續(xù)寫(xiě)下去,讓這部小說(shuō)充滿(mǎn)生機(jī)。寫(xiě)湘西的美食時(shí),光寫(xiě)一道菜,他都可以寫(xiě)幾頁(yè)。當(dāng)他發(fā)現(xiàn)這個(gè)東西對(duì)他很重要,就會(huì)一直寫(xiě)下去。當(dāng)我們看這些的時(shí)候,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這些現(xiàn)在看似普通的東西,對(duì)那個(gè)年代來(lái)說(shuō)卻很重要,同時(shí)跟現(xiàn)在也會(huì)有一些銜接。
張新穎:汪曾祺的一封信里說(shuō)過(guò):“黃永玉對(duì)事物多情。”多情才可以記這么多年。當(dāng)我們談到黃永玉以“不選擇”的方式寫(xiě)作的時(shí)候,可能會(huì)覺(jué)得很啰唆,其實(shí)不是這樣的。
我給大家講一個(gè)特別不啰唆的地方,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有這么一段:主人公序子12歲時(shí)因?yàn)樵诩亦l(xiāng)沒(méi)法待下去了,就出來(lái)找爸爸。他爸爸在軍隊(duì)里面有一個(gè)閑差,可讓小孩待在部隊(duì)也不行,他爸爸就讓一個(gè)叔叔帶他到廈門(mén)集美學(xué)校念書(shū)。序子聽(tīng)到這個(gè)事,心想爸爸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,本來(lái)準(zhǔn)備回去埋怨一下爸爸。可是當(dāng)他看到爸爸心情很黯然時(shí),反倒來(lái)勸爸爸,跟他講讀書(shū)怎么怎么好,講了很長(zhǎng)很長(zhǎng)一段,寫(xiě)了好幾頁(yè),他爸爸一句話沒(méi)說(shuō)。第二天爸爸送他到長(zhǎng)途汽車(chē)站,還是一句話沒(méi)說(shuō)。一個(gè)“啰里啰唆”的作品,可是寫(xiě)父子分別的時(shí)候,卻寫(xiě)到他爸爸一個(gè)字都沒(méi)說(shuō),我覺(jué)得真的是一種心境。一個(gè)字不寫(xiě),勝過(guò)千言萬(wàn)語(yǔ),表現(xiàn)力太強(qiáng)大了。看起來(lái)寫(xiě)的不用心,其實(shí)是有對(duì)應(yīng)關(guān)系的。
一個(gè)文學(xué)的奇跡
李輝:講到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·八年》,黃永玉是在有意識(shí)地用一些閩南方言,后面再加一個(gè)注。安溪的朋友看完《八年》(上)的時(shí)候,都說(shuō)沒(méi)想到離開(kāi)安溪70多年的黃永玉,閩南話還說(shuō)得那么好。他廣東話也講到很好,上海話也會(huì)講一些。一個(gè)人的語(yǔ)言好壞與他對(duì)語(yǔ)言的感覺(jué)是密切相關(guān)的,多少年后,還能記得當(dāng)年所待過(guò)地方的一句土話。現(xiàn)在很多作家很會(huì)講故事,但是對(duì)語(yǔ)言的磨煉、講究,還是不太重視。黃永玉有一顆年輕人的心態(tài),寫(xiě)完小說(shuō),他也會(huì)看電視,什么都看,比如看《非誠(chéng)勿擾》,了解現(xiàn)在年輕人的戀愛(ài)觀和生命狀態(tài),對(duì)新鮮事物感到非常好奇,這和他創(chuàng)作是有關(guān)系的。他和現(xiàn)在的社會(huì)沒(méi)有脫節(jié),這也是他生機(jī)勃勃的一個(gè)表現(xiàn)。我覺(jué)得他的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還可以達(dá)到一個(gè)更高的層次。周毅先生講過(guò)一句話:“這部小說(shuō)很可能打破了我們現(xiàn)有的文學(xué)史對(duì)小說(shuō)格局的判斷。”
張新穎: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》,其實(shí)是一個(gè)老者與不同生命階段的自己對(duì)話。其中既有孩子的視角,也有老人的視角,多重視角交錯(cuò)在一起。另外,黃永玉的設(shè)想讀者是他的前輩。如果表叔沈從文在看,如果蕭乾在看,他們的感覺(jué)會(huì)怎么樣?這個(gè)很獨(dú)特,因?yàn)楹芏嘧骷以O(shè)想的讀者是現(xiàn)代的讀者或者將來(lái)的讀者。
對(duì)20世紀(jì)的人來(lái)說(shuō),每個(gè)人的生命經(jīng)驗(yàn)都非常豐富,可是我們很少有寫(xiě)這么漫長(zhǎng)經(jīng)驗(yàn)的小說(shuō)。如果有的話,這個(gè)漫長(zhǎng)的生命經(jīng)驗(yàn)往往成了一個(gè)時(shí)代的主角,隨著時(shí)代的變動(dòng)而變動(dòng),最后變成時(shí)代的受害者。我們常常聽(tīng)到這樣的事,我被“上山下鄉(xiāng)”害了,我被”文革”害了,再往前一點(diǎn),被戰(zhàn)爭(zhēng)害了。可是黃永玉也經(jīng)歷了這些事情,他卻從來(lái)沒(méi)有恨過(guò),也沒(méi)有被毀掉。個(gè)人的生命不再是時(shí)代變化的主角,不再是時(shí)代變化的一個(gè)例證,僅僅是一個(gè)個(gè)人的成長(zhǎng)史。他跟這個(gè)時(shí)代變化有密切的關(guān)系,但又沒(méi)被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變化淹沒(méi)。我們其實(shí)需要慢慢地拆除我們腦子里各種各樣的觀念,關(guān)于生命的觀念,關(guān)于什么是文學(xué)的觀念,關(guān)于小說(shuō)應(yīng)該是什么樣的觀念。把這些東西拆除之后,才有可能越來(lái)越深地來(lái)感受這部作品。我覺(jué)得這部小說(shuō)將來(lái)會(huì)獲得比現(xiàn)在更高的認(rèn)可。
李輝: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·朱雀城》像是一部寫(xiě)故鄉(xiāng)的小說(shuō),《無(wú)愁河的浪蕩漢子·八年》像是一部寫(xiě)流浪的小說(shuō),現(xiàn)在寫(xiě)到福建部分,馬上又要寫(xiě)江西,江西到上海,然后是臺(tái)灣、香港,完全是一種流浪的生活,最終回到北京。你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他東西越寫(xiě)越多,在寫(xiě)的過(guò)程中不斷滋養(yǎng)自己,把自己融入作品中去,繼續(xù)往前走。現(xiàn)在小說(shuō)寫(xiě)不寫(xiě)完,對(duì)黃永玉來(lái)講已經(jīng)不是很重要,他的創(chuàng)作,本身就是一個(gè)文學(xué)的奇跡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