吉狄馬加:寫在天空和大地之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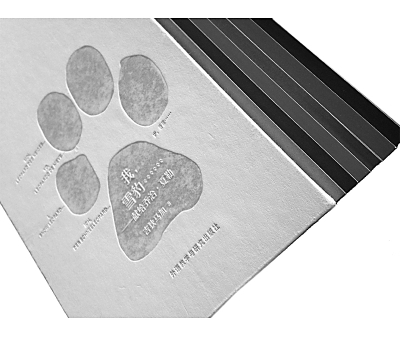
【翹楚】
“彝族是一個充滿詩的民族,數(shù)量驚人的創(chuàng)世史詩和古老民歌是吉狄馬加詩歌創(chuàng)作的不竭源泉。那綿延不絕的群山,翱翔于群山之巔的雄鷹,纏著英雄結(jié)的男人,扭動腰肢的姑娘,鱗次櫛比的瓦板房,月琴動人的吟唱,更為詩人打開了想象的翅膀。吉狄馬加在《服務(wù)與奉獻》中寫道:如果作家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神性背景,那么蒼茫的大小涼山就是我精神的家園……如果說我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符號,我承認我是在延續(xù)著一種最古老的文明。——題記”
2016年6月,詩人吉狄馬加收獲了2016年度歐洲詩歌與藝術(shù)荷馬獎。頒獎儀式特意選擇在吉狄馬加的故鄉(xiāng)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舉行。
領(lǐng)獎時,吉狄馬加難掩激動——
“感謝歐洲詩歌與藝術(shù)荷馬獎評委會,你們的慷慨和大度不僅體現(xiàn)在對獲獎?wù)呷縿?chuàng)作和思想的深刻把握,更重要的是你們從不拘泥于創(chuàng)作者的某一個局部,而是把他放在了一個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坐標高度。”
對于當今詩壇,吉狄馬加有著自己的理解。在他剛開始寫詩的年代,朦朧詩初興,詩歌刊物的發(fā)行量達上百萬份,一首詩可以讓詩人家喻戶曉。如今,雖然詩壇已經(jīng)不復(fù)當年的繁盛,但他仍然認為“目前中國詩歌狀態(tài)是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”。寬松的文化氛圍,自由的創(chuàng)作思想、表達內(nèi)容和藝術(shù)手段,為詩歌創(chuàng)作提供了無限的可能。
詩之源
很多人認識吉狄馬加,始于他的那一聲呼喊,“啊,世界,請聽我回答/我—是—彝—人”(《自畫像》)。這個來自四川大涼山的彝族青年,在20世紀80年代一步入詩壇,就因詩中強烈的民族使命感、獨屬于彝人的豐富感情和色彩,引起眾人的關(guān)注。然而,這個年輕詩人的目光并未囿于家鄉(xiāng)山水,雙腳站在大涼山土地上的他,視線投向的是遠方的世界。
生于1961年的吉狄馬加,可謂年少成名。當?shù)谝槐驹娂冻鯌俚母琛窋孬@中國第三屆新詩(詩集)獎時,他年僅26歲,與其同時獲獎的還有朦朧詩的代表人物北島。從《星星》詩刊脫穎而出,到獲得新詩(詩集)獎,再到組詩《自畫像及其他》獲第二屆全國少數(shù)民族文學(xué)詩歌獎一等獎,僅是數(shù)年間的事。
鄧友梅初讀吉狄馬加的詩歌一時“失神忘我”,覺得有種“說不清道不明的思緒和神韻在心中升騰”,他相信,這是只有彝人自己才能寫出的詩歌。
從創(chuàng)作之初,吉狄馬加就一直對一個問題苦苦求索:為什么很多民族人口很少,處于主流文化的邊緣,卻能產(chǎn)生世界級的作家?為此,他開始了大量閱讀。在祖先的“這個世界”之外,他從外國文學(xué)寶庫中找到了自己詩歌的“另一個世界”。
2001年,吉狄馬加在《民族文學(xué)》和《世界文學(xué)》發(fā)表文章《尋找另一種聲音》,記錄了對他產(chǎn)生深刻影響的世界級作家和作品。
普希金是吉狄馬加的啟蒙者,這位俄羅斯詩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和良知給了他強烈的震撼,灌溉了他的詩人夢想。而非洲裔黑人作家和非洲本土黑人作家則給予他最多的心靈共振,改變了他對文學(xué)價值的判斷。
也正是這個時候,吉狄馬加開始真正關(guān)注彝族本土文化,意識到“每一個民族都有生存和發(fā)展的權(quán)利,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可替代的”。拉丁美洲魔幻現(xiàn)實主義文學(xué),更為他探究彝民族歷史、神話和傳說帶來啟示。
早在加西亞·馬爾克斯的《百年孤獨》獲得諾貝爾文學(xué)獎之前,這部作品就深深觸動了吉狄馬加。當時,馬爾克斯的作品在中國并不暢銷,“我們完全是憑著一種直覺,開始關(guān)注馬爾克斯等拉美作家的作品。”藏族作家扎西達娃常與他討論拉丁美洲文學(xué)給彼此帶來的新鮮感受,為這些作品超越地域局限,具有更廣闊的全人類的視野感到震撼。
這群生活在邊緣地帶的少數(shù)民族作家和詩人野心勃勃:“一定要把自己的文學(xué)標桿的制定放在整個世界而不僅僅是在中國”。
吉狄馬加相信,一個詩人要真正成長,就必須受到多種文化的影響和養(yǎng)育。他將此概括為“縱的繼承”和“橫的移植”。“縱的繼承”是從本民族的歷史文化、中國數(shù)千年所形成的偉大文學(xué)傳統(tǒng)中吸取養(yǎng)分,“橫的移植”就是向世界各國、各民族優(yōu)秀文學(xué)學(xué)習(xí)、借鑒。
2008年10月,在“當代世界文學(xué)與中國”國際學(xué)術(shù)研討會上,吉狄馬加在談及對中國詩人寫作產(chǎn)生深刻影響的外國詩人時,列舉了一長串名字,詩人伊沙對此印象非常深刻。他一直覺得自己的記憶力好,卻也想不出來一個需要補充的,不禁興奮地對與會的女詩人瀟瀟說:吉狄馬加的發(fā)言太好了,等于是代表幾代中國詩人向這些偉大的名字致敬。
大目標讓詩人有了大格局,廣涉獵給詩歌增添了新厚度。20世紀90年代以后,吉狄馬加的詩歌褪去青澀,不斷拓展表達疆域,除了反復(fù)提到家鄉(xiāng)的土地、彝族的同胞外,也逐步深化了他的人文情懷與世界主題。
詩人西川評價吉狄馬加:“世界政治、文化、歷史視野,在整個當代中國詩歌界都是罕見的”。面向世界成為這位彝族詩人寫作中的一個重要的、與眾不同的特征。
立陶宛詩人托馬斯·溫茨洛瓦稱吉狄馬加為民族詩人和世界公民。這個彝族詩人的筆深深地植根于養(yǎng)育了自己民族的大地的子宮中,而飛翔的翅膀卻又越過大涼山脈,跨越國界、民族,創(chuàng)造屬于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。西川說:“對吉狄馬加來說,家鄉(xiāng)和遠方毗鄰而在。”
詩之韻
2010年3月,在“光明的歌者”艾青百年誕辰紀念詩歌朗誦會上,吉狄馬加的演講雋永深情——
“我愛戴并且由衷地敬仰艾青。從踏上詩歌的道路,我就一直是艾青的追隨者,猶如在混沌中跟隨一支火炬前進。”
艾青詩歌中特有的苦難與愛的氣質(zhì),滲透進吉狄馬加的詩歌底色中,艾青詩歌主題中對光明的渴望、對歷史的關(guān)切、對真理的敬仰、對自由的禮贊,也在吉狄馬加的詩歌中被反復(fù)吟唱。
鐘情于精神,沉醉于使命,吉狄馬加像艾青一樣,手持火炬在詩歌王國中行走,他的詩歌不是朝向狹隘自我的竊竊私語,而是面向大眾的黃鐘大呂。
“今天許多詩人太關(guān)注自己眼皮底下的事,但對人的生存狀態(tài)和人類的命運卻少有關(guān)注,這是我們必須改變的。”
詩人對詩人的認同,也是自己詩歌的標記。吉狄馬加只熱愛“詩歌疆域里的雄獅”。2016年3月,他重新研讀俄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詩歌,并為其中的代表人物馬雅可夫斯基寫下400余行的長詩——《致馬雅可夫斯基》。
這個俄羅斯文學(xué)白銀時代的偉大詩人繼承了普希金的史詩傳統(tǒng),用如椽之筆見證了風(fēng)起云涌的時代,掀起了一場席卷人們精神世界的抒情風(fēng)暴。
“你的紀念碑高大巍峨——誰也無法將它毀滅/因為它的鋼筋,將根植于人類精神的底座”
《致馬雅可夫斯基》
對馬雅可夫斯基進行詩歌式的追認,正是對其詩歌價值的認同與呼喚。長詩中,吉狄馬加一并羅列了很多名字,將他們歸為同一陣營,巴勃羅·聶魯達、巴列霍、阿蒂拉、奈茲瓦爾、希克梅特、布洛涅夫斯基……這個來自東方的現(xiàn)代詩人遙望星河,追憶這些遠去的同行者。
復(fù)蘇一個大陸的命運與夢想,抒發(fā)恢弘壯闊、灼熱的情感,將個人憂思與時代、歷史、未來、世界連接在一起,正是吉狄馬加的詩歌特質(zhì)。他認為——
“詩歌應(yīng)該具有見證的意義。它是詩人對思想、靈魂乃至宇宙萬物的感受,它有時就如同一束光,而這束光能刺穿時間和歷史的厚度。”
在吉狄馬加看來,只有成為一個民族和時代的見證人,才能真正擔(dān)當起這個民族和時代精神的詮釋者。
法國詩人雅克·達拉斯將此描述為“以高山上雄鷹的視力,明察平原上的現(xiàn)代變化”。在吉狄馬加的詩中,充滿了對暴力與武裝侵略的激憤,對歧視、排斥的反抗,對和平的強烈渴望,對人類平等的信仰,“對包括巖石、河流、山脈、云彩、空氣、水、火、土地等所有的生命都有靈魂的確信。”(委內(nèi)瑞拉學(xué)者、詩人布利塞尼奧·格雷羅語)
面對大時代、大事件,吉狄馬加也從不失語。在他看來,詩歌的秘密在于“絕不回避現(xiàn)實,關(guān)注發(fā)展與未來”。永恒的主題和時代的命題相互碰撞,一首首具有精神高度、又能見證時代的經(jīng)典之作孕育而生。
2010年青海玉樹發(fā)生地震后,吉狄馬加第一時間趕赴災(zāi)區(qū),他為藏族人民在面對苦難與離別時的獨特信仰而深深感動。地震過去一個多月后的一天晚上,吉狄馬加走到玉樹的嘉那嘛呢石經(jīng)城。那里由25億塊嘛呢石堆放而成,是目前全世界人工堆放石頭數(shù)量最多的石堆,每一塊嘛呢石上都刻有六字箴言和經(jīng)文。
吉狄馬加一直記得那個夜晚——
“天空群星燦爛,很遠處好像有白塔在慢慢上升,群山好像慢慢變得透明,野外的牦牛都像水晶一樣。這個時候,我告訴自己,要寫一首《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》獻給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,他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,他們的愛和生命與這片土地緊緊相連。”
詩人回到帳篷用兩個小時寫了初稿,第二天四點就起床,又用了三個小時把這首詩完成。吉狄馬加最愛在黎明的時候?qū)懺姡按蟾旁诶杳鞯臅r候所有生命都在蘇醒,在那樣一個時候我會聽見詩歌在內(nèi)心召喚,我能真切地感受到,我需要找到更好的語言,在沒有瞬間遺忘的時候把它寫下來。”
2013年,長詩《我,雪豹……》問世,詩人葉延濱稱它為吉狄馬加的標志性作品。
雪豹,一種瀕危的貓科動物,它們離群索居,遠離人跡,孤傲地生活在雪線附近,是世界上最高海拔的象征。三江源是目前全世界雪豹分布最集中的地方,有五六千只。野生動物學(xué)家喬治·夏勒長期在青海追尋和考察雪豹的生存狀況,吉狄馬加與他有過多次接觸,非常崇敬他的付出。
長詩也是對這位杰出動物學(xué)家的致敬。詩人借由雪豹的獨白叩問存在的意義,表達了對自然的敬畏,對獨立人格的堅守和對永恒的追問。
與《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》一樣,《我,雪豹……》是長期醞釀、迅速寫就的作品。400余行的長詩,真正進入寫作階段,只用了四天半的時間。吉狄馬加將這首詩歌的成功歸功于強大的精神背景。“只有思想武裝起來了,我們才能用筆去觸摸事物的本質(zhì)。”
對于詩壇上一些人為寫詩而創(chuàng)作,沉湎于象牙塔里的遣詞造句,偏執(zhí)于技術(shù)形式的矯揉造作,吉狄馬加并不贊同。他認為,詩歌永遠不應(yīng)失去對文化、社會、生存和人性的觀照。相比那即逝的情緒、縹緲的玄思,他更看重厚重的思考、真誠的抒發(fā)。詩歌應(yīng)超越一般性閱讀和審美的范圍,超越語言和修辭學(xué)方面固有的意義,作為一種精神象征引領(lǐng)人類從熙熙攘攘的世界走向一個更為高明的高地。它不應(yīng)是“貴婦的寵物”,而應(yīng)“寫在天空和大地之間”。
詩之語
2015年,吉狄馬加離開工作9年的青海,重新回到工作過11年的中國作協(xié),擔(dān)任中國作協(xié)副主席、書記處書記。
在面對眾多媒體的采訪時,吉狄馬加很難回避一個問題,“如何平衡詩人與官員兩種身份?”他并不掩飾對多次回答這個問題的無奈。于他而言,行政工作是他的職業(yè),而寫詩不是。“把寫詩說成是一種職業(yè),我認為是可笑的行為。”
在吉狄馬加生活的高原和民族中,詩人是被神所選擇的具有靈性的人,詩人更像是一個角色,是精神的代言人。通過充滿靈性的寫作,力求與自己的靈魂、現(xiàn)實乃至世間的萬物進行深度對話。
“我接受有關(guān)我‘身份’的任何稱謂,但我作為一個詩人的‘身份’,將穿越我生命的所有的生和全部的死。”
任青海省委常委、宣傳部部長期間,吉狄馬加沒有放棄詩歌,并且創(chuàng)作了不少作品。他感慨,青海這片土地歷史文化豐厚,給予他很多滋養(yǎng),一方面提升了他的思想高度,一方面提供了思考問題的載體。“有機會到青海工作9年是我的幸運,這對我以后的創(chuàng)作都會有極大的影響。”
青海湖國際詩歌節(jié)的創(chuàng)辦更證明了吉狄馬加“兩種身份”的互為補益。創(chuàng)辦一個具有世界地位和國際品質(zhì)的現(xiàn)代詩歌節(jié)一直是他的夢想。
早在1997年,吉狄馬加就參加過哥倫比亞麥德林國際詩歌節(jié),那是南美最大的國際詩歌節(jié),同時也是目前國際上影響最大的詩歌節(jié)之一。詩歌節(jié)的盛況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,他立志回到中國后也要創(chuàng)辦一個面向世界的詩歌節(jié)。“我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聚會,能像一個詩歌節(jié)那樣給人和生活帶來希望和夢想。”
2007年,由吉狄馬加倡導(dǎo)發(fā)起,在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領(lǐng)導(dǎo)的支持下,青海湖國際詩歌節(jié)成功舉辦。來自34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200多位詩人會聚青海湖畔。第二年,參會詩人擴展到50多個國家和地區(qū)。
迄今為止,青海湖國際詩歌節(jié)已成功舉辦四屆,國內(nèi)外影響巨大,累計有近160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1000余名詩人參加,被稱為世界上第七大國際詩歌節(jié)。
在吉狄馬加的努力下,青海湖國際詩歌節(jié)、青海國際詩人帳篷圓桌會議、達基沙洛國際詩人之家寫作計劃、諾蘇藝術(shù)館暨國際詩人寫作中心對話會議、三江源國際攝影節(jié)、世界山地紀錄片節(jié)、青海國際水與生命音樂之旅以及青海國際唐卡藝術(shù)與文化遺產(chǎn)博覽會已經(jīng)成為中國進行國際文化交流和對話的重要途徑。
吉狄馬加注重詩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獨特作用。他的詩歌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文字,他多次率領(lǐng)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,與國際文學(xué)界對話與交流。無論是其詩歌被翻譯的外語語種的數(shù)量,還是其本人在國際詩壇上的亮相頻次,在中國詩人中都非常突出。
有人認為,真正的詩不可翻譯,詩就是在翻譯過程中失去的那個部分。吉狄馬加承認,詩歌翻譯是一門遺憾的藝術(shù),但當詩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時候,又會找到新的活力和生命。“人類對詩歌的翻譯一天也未停止。”
詩之魂
“作為人類精神文化代言人的作家和詩人,我們必須標明自己的嚴正立場,并將身體力行地捍衛(wèi)人類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。”“身體力行”確實是吉狄馬加區(qū)別于其他詩人的重要特質(zhì)。
學(xué)者張清華評價吉狄馬加:“在當代詩人中,也許像馬加那樣寫出了優(yōu)秀作品的詩人并不少見,但像他那樣努力踐行而且實現(xiàn)著詩歌中愛與光明、人類精神的融通交匯、生命尊嚴與文化多樣性的維護的文化理想的詩人,卻堪稱鳳毛麟角。”
在工業(yè)化社會消弭差異,消費時代瓦解信仰的今天,每年都有無數(shù)種語言在消失,有不少民族的文化都面臨著難以傳承的危險。面對這一現(xiàn)象,吉狄馬加在多個場合表達了自己的憂慮與關(guān)切。
長詩《我,雪豹……》中詩人借雪豹之口吶喊:“我的歷史、價值體系以及獨特的生活方式/是我在這個大千世界里/立足的根本所在,誰也不能代替!”
吉狄馬加也如雪豹一樣,以殉道者般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,忠誠守衛(wèi)著受現(xiàn)代文明威脅的文化生命力。
2014年,吉狄馬加獲得姆基瓦人道主義大獎,被授予“世界性人民文化的卓越捍衛(wèi)者”稱號,他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中國作家和詩人,也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亞洲人。
法國詩人雅克·達拉斯稱吉狄馬加是一位既含蓄有致又勇于行動的詩人,只用不多的話語就能把詩的氣息傳向遠方的詩人。這也許得益于他曾用腳步丈量過世界的很多角落,呼吸了來自不同地方的詩歌的空氣。
吉狄馬加曾在普希金生活過的地方進行虔誠的探訪,在帕斯捷爾納克的墓地守候了兩小時;在塞爾維亞的貝爾格萊德,他專門抽時間與當時還在世的米洛拉德·帕維奇長談了一個多小時;在智利,他來到巴勃羅·聶魯達的墓地祭拜,聽消失了的卡爾斯卡爾的印第安人族群的悲傷往事……
吉狄馬加承認,真正保持一種屬于自己的閱讀和寫作習(xí)慣,對一個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在聚光燈下的人來說很難。但他需要通過閱讀來提高自己的思想深度,以更高遠的視角,去觀望和回望自己民族的生活,審視自己民族的歷史。
“真正的詩人,在離開這個喧囂的世界之前,我想也只有詩能給他帶來片刻的寧靜。詩或許就是一種從生到死的莊嚴儀式。詩人在寫作時,靈魂和心靈都是寂寞的。我也是。”
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,吉狄馬加就離開了大涼山,在不同的地方書寫著自己的人生故事。但故鄉(xiāng)一直在他的心頭縈繞。于他而言,彝族的酸菜湯、坨坨肉,終生難忘。“只要有機會,我都會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詩人那樣,一次次地回到自己的故鄉(xiāng),在那里尋找并獲得永不枯竭的靈感。”他不無痛心地提到,大小涼山仍然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區(qū)之一,他會積極地參與到為故鄉(xiāng)消除貧困的工作之中,盡自己的一份努力。
我寫詩,是因為我的憂慮超過了我的歡樂。
我寫詩,是因為我想分清什么是善,什么又是惡。
對人的命運的關(guān)注,哪怕是對一個小小的部落做深刻的理解,它也是會有人類性的,我對此深信不疑。
我寫詩,是因為在現(xiàn)代文明和古老傳統(tǒng)的反差中,我們靈魂的陣痛是任何一個所謂文明人永遠無法體會得到的。
《一種聲音——我的創(chuàng)作談》
吉狄馬加很喜歡雅羅斯拉夫·塞弗爾特的一句詩:“要知道搖籃的吱嘎聲和樸素的搖籃曲,還有蜜蜂和蜂房,要遠遠勝過刺刀和槍彈。”他覺得這說出了世界上所有詩人的心聲。
雖然面臨很多困難,但吉狄馬加從來沒有喪失過對詩歌的信心,他相信只有詩歌能讓人們辨別出正確的方向,找到通往人類精神故鄉(xiāng)的回歸之路。“詩歌永遠是黑暗中的火把,是為我們擦去眼淚和悲傷的那一雙溫柔的手。”
作為一個詩人,吉狄馬加最大的夢想是在自己的創(chuàng)造力還沒有枯竭之前,能寫出一批可與大詩人比肩的史詩級作品。“我以為在任何時代,都會有人在傾聽詩人的聲音。”
2016年3月,在希臘雅典舉行的希文版吉狄馬加個人詩集簽名發(fā)行儀式上,他面對記者的提問時說:“中國詩歌今天達到的高度,毫無懸念將高于其他的藝術(shù)門類。”他堅信:“詩歌的存在是人類邁向明天最真實的理由。”
吉狄馬加,彝族,詩人、作家。1961年生于四川大涼山。1982年畢業(yè)于西南民族大學(xué)中文系。現(xiàn)任中國作家協(xié)會副主席、書記處書記,兼任中國少數(shù)民族作家學(xué)會會長,中國詩歌學(xué)會顧問。
(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)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