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都在伊犁生活 ——讀艾克拜爾·米吉提散文集《伊犁記憶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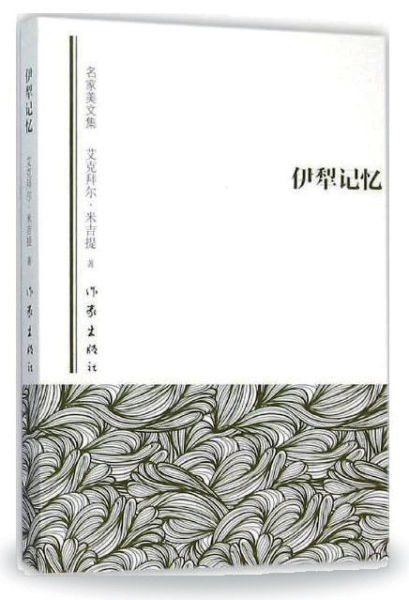
當(dāng)哈薩克族作家艾克拜爾·米吉提把他的最新散文集命名為《伊犁記憶》時,我把它理解為這是作者對伊犁故鄉(xiāng)的回望,也是他對曾經(jīng)生活記憶的梳理。而我這個在伊犁生活過近10年的讀者讀起來,也算是一種回望,是對過往伊犁風(fēng)情的回望。
上世紀(jì)70年代末,艾克拜爾以短篇小說《努爾曼老漢和獵狗巴力斯》走上文壇,這篇小說獲得了1979年全國優(yōu)秀短篇小說獎。可以說,他的文學(xué)之路,由此正式開始。而此時,艾克拜爾還是伊犁州黨委宣傳部的一名干部。不久之后,他去北京領(lǐng)獎。到了北京才聽說已經(jīng)被文學(xué)講習(xí)所(即現(xiàn)在的魯迅文學(xué)院)錄取,成了文學(xué)講習(xí)所第五期的一名學(xué)員,多年后他又成了魯迅文學(xué)院的學(xué)員導(dǎo)師。
這些經(jīng)歷,他都寫進(jìn)了《從學(xué)員到導(dǎo)師》一文中。我在看這篇文章時難免會想起2013年我在魯迅文學(xué)院就讀時接觸艾克拜爾老師的情景。那時,我因為在詩歌組,未拜入他的門下,有一天他請他的學(xué)生和我們幾個新疆籍學(xué)員吃飯,老鄉(xiāng)見老鄉(xiāng),于是就喝得盡興了。這是在看這本書時想起的一些往事。恰巧,這也是一本多半寫往事的書,從《伊犁記憶》《王蒙老師剪影》《伊犁散記》《童年記憶》《初次遇狼》等文章的題目即可印證。
本書開篇就是《伊犁記憶》。文章的第一句話就說出了多少在外的伊犁人的心聲:伊犁是一種記憶。看過文章就可知曉,這種記憶不僅屬于離開伊犁的游子,也屬于依舊生活在伊犁的“土著”和初來這片土地生活的人。起碼如我,大學(xué)畢業(yè)后即生活在此,讀老伊犁人的文章,也常能生出不少回憶。
在艾克拜爾兒時的記憶中,“這是一個生滿白楊的城市。那密布城市的白楊樹,與云層低語……樹下是流淌的小河,淙淙流入庭院,流向那邊的果園……”這在上世紀(jì)五六十年代在伊犁出生的人記憶中,真是再常見不過了。所以,伊犁州的首府伊寧市,也曾被叫作“白楊城”。袁鷹先生曾經(jīng)游歷伊犁,更是寫下了散文名篇《城在白楊深處》,由此可見當(dāng)時的白楊之盛。七八十年代在伊犁出生的人,可能還會看到一點點尾巴。而作為我這樣一個外來者,所來不過10年,即便在初到伊犁時,曾經(jīng)因為職業(yè)之便走遍了城市的角角落落,也見過一些殘存的白楊和果園,近幾年來是愈漸難見了。這樣的情形,艾克拜爾每次回鄉(xiāng)時也都有切身的感受,寫進(jìn)了文章。
在作者的伊犁記憶里,除了白楊,還有滿眼的各色花草,“每當(dāng)夜幕降臨,從那家家戶戶落滿芬芳的花園里便會傳來百靈鳥不倦的鳴囀。”每家每戶庭院、果園里,在花季花開各色,讓初來這座小城的人忍不住驚嘆,進(jìn)入了“花城”。這樣的記憶對于在伊犁生活得久一些的人來說,真的是怎么也磨滅不掉的,即便離開故鄉(xiāng)二三十年后,作者想起這些,還依舊溫馨如昨。所以在他看來,“伊犁春色的真正標(biāo)志,是那漫山遍野怒放的郁金香”,要知道,伊犁本是郁金香的原產(chǎn)地。也是看了這本書,我才知道,原來被維吾爾人稱為“萊麗哈薩克”的郁金香早已經(jīng)融入了哈薩克人的血液,是哈薩克人最喜歡的花。
一個出門在外的人,走到哪里,看到什么都會把它拿來和故鄉(xiāng)的風(fēng)物進(jìn)行比較。艾克拜爾也不例外,他在每次在北京郊游,看到山溝里流淌的細(xì)小的河流,便會想起故鄉(xiāng)天山深處的每一條溪流來。喝著伊犁出產(chǎn)的白酒,端起酒杯也會忍不住說一句:“請開懷暢飲,這是伊犁河的水……”書中絕大部分筆墨都是關(guān)于新疆的,《歌者與〈瑪納斯〉》《作為文人的賽福鼎·艾則孜》《天山腳下的哈薩克人》等篇章同樣值得留意。
也正因為如此,我這樣一個曾生活在伊犁的讀者讀本書時,認(rèn)為全書最好的文章就是寫伊犁的那幾篇,估計作者不一定會認(rèn)同,其他讀者更不一定認(rèn)同。這些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們都曾在伊犁生活過。
書中還有一篇《巴金先生的一封回信》也引起了我的注意,這篇不長的文章讓我意識到,巴金等著名作家作品的維吾爾文、哈薩克文譯本的相關(guān)研究應(yīng)該還有很多未墾之地,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相關(guān)著作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