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一個(gè)輪回在開(kāi)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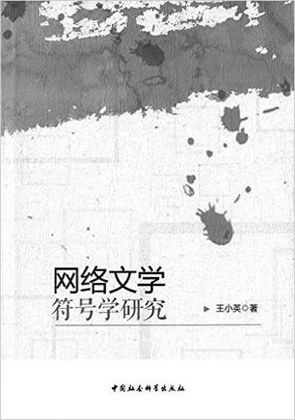
《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的符號(hào)學(xué)研究》,王小英著,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,59.00元
有不少人認(rèn)為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與書(shū)面文學(xué)的不同只是發(fā)行傳播方式的不同,現(xiàn)在看來(lái)這種傳播方式的巨大差別,必然導(dǎo)致一種新的文學(xué)的產(chǎn)生。它的歷史重要性,完全可以比擬四百年前啟蒙時(shí)代書(shū)面印刷文學(xué)對(duì)文學(xué)史的沖擊,完全可以比擬小說(shuō)的崛起。
我們面臨的,不是一種從來(lái)不缺的下里巴人俗文學(xué),或是一種舶來(lái)的時(shí)髦媚俗。十幾年之中,一個(gè)稀有文化物種,在我們眼前長(zhǎng)成一個(gè)龐然大物,使文學(xué)研究者瞠目結(jié)舌,讓文化觀察者欣喜若狂。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不是一個(gè)世界性潮流,而是中國(guó)特有的文化現(xiàn)象,這是我們翻開(kāi)這本書(shū)就讀到的令人驚異的事實(shí),據(jù)說(shuō)可能只有韓國(guó)可以比擬,日本差強(qiáng)人意,其他各國(guó)均無(wú)。
這是很令人驚異的事,中國(guó)人,尤其是中國(guó)青少年群體,可以具有超常的文化創(chuàng)新能力,就看我們是否能面對(duì)。既然是世界獨(dú)有,這個(gè)中國(guó)當(dāng)代文化研究的大題目,就需要一個(gè)獨(dú)特的理解。西北師范大學(xué)王小英教授的這本書(shū),提供了一個(gè)杰出的系統(tǒng)的理解方式,這個(gè)怪異萬(wàn)端的龐然大物,被庖丁解牛般剖析開(kāi)來(lái);這個(gè)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奇文化現(xiàn)象,頓時(shí)變得條理分明,可解可讀。
王小英牽住了這頭怪獸的牛鼻子:那就是,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(shuō)作為一種媒介的形式。所有五花八門(mén)的新問(wèn)題,甚至內(nèi)容龐雜多變,奇幻魔幻科幻,言情無(wú)情濫情,包括它的言辭挑釁卻道德保守,甚至其創(chuàng)作方式(王小英稱之為“間性編碼調(diào)控”),它的平臺(tái)批量生產(chǎn),所有這一切,都來(lái)自它的傳播方式:屏上閱讀,即時(shí)消費(fèi)。由此產(chǎn)生了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的許多奇怪而且日新月異的做派,例如投票,推薦,點(diǎn)擊率、點(diǎn)贊、點(diǎn)評(píng)、打賞,加入門(mén)派,加入粉絲團(tuán)——中國(guó)青少年們幾乎在玩網(wǎng)絡(luò)游戲一樣玩弄文學(xué)。可以說(shuō)這些讀者反饋,在傳統(tǒng)書(shū)面文學(xué)的閱讀中也不是不可能。但是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的互動(dòng),是與創(chuàng)作同時(shí)發(fā)生的,此時(shí)此地在影響創(chuàng)作,甚至直接指揮小說(shuō)往下章節(jié)的寫(xiě)法。
因此,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是用部分回到過(guò)去,大步跨向未來(lái),來(lái)占領(lǐng)此刻:在口頭敘述時(shí)代,聽(tīng)眾集體在場(chǎng)消費(fèi)故事;在書(shū)面文本時(shí)代,讀者個(gè)別地不在場(chǎng)消費(fèi)故事;在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時(shí)代,網(wǎng)民集體性“擬在場(chǎng)”(即雖然人身不在場(chǎng),意義行為卻在場(chǎng))消費(fèi)故事。消費(fèi)的在場(chǎng)性與集體性是口頭文學(xué)的特征,因此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以全新的方式,部分回向了口頭文學(xué)的消費(fèi)方式。
不僅如此,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文本的邊界不清,卷入大量“伴隨文本”,這點(diǎn)看來(lái)也在返回口頭文學(xué)。一場(chǎng)口頭演出,例如說(shuō)書(shū),其“文本”遠(yuǎn)遠(yuǎn)不止是語(yǔ)言,還包括腔調(diào)、姿勢(shì)、表情、燈光、聽(tīng)眾的臨場(chǎng)反應(yīng)(罵與贊),以及最重要的,講故事者與聽(tīng)眾的互動(dòng),對(duì)故事隨機(jī)應(yīng)變的調(diào)整。其結(jié)果是:口頭敘述與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的文本邊界非常模糊,進(jìn)入解釋的“全文本”邊界難以劃定。而正成對(duì)比的是:書(shū)面文本的邊界非常清楚,不僅印刷、紙質(zhì)、包裝等不能算,連標(biāo)題等也是“副文本”。
這是一種全新的文學(xué)。有不少人認(rèn)為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與書(shū)面文學(xué)的不同只是發(fā)行傳播方式的不同,現(xiàn)在看來(lái)這種傳播方式的巨大差別,必然導(dǎo)致一種新的文學(xué)的產(chǎn)生。它的歷史重要性,完全可以比擬四百年前啟蒙時(shí)代書(shū)面印刷文學(xué)對(duì)文學(xué)史的沖擊,完全可以比擬小說(shuō)的崛起。無(wú)怪乎王小英此書(shū)發(fā)現(xiàn),被許多思想家認(rèn)為屢試不爽的“四體演進(jìn)”,在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上很奇怪地不起作用了:弗萊認(rèn)為1500年以來(lái),小說(shuō)的發(fā)展在現(xiàn)代早已經(jīng)進(jìn)入最后一個(gè)階段,反諷階段。王小英發(fā)現(xiàn)情況不對(duì),反諷忽然不見(jiàn)了(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哪怕充滿搞笑,絕大部分是“可靠敘述”),英雄與羅曼史時(shí)代似乎又開(kāi)始了:
“弗萊(NorthropFrye)在《批評(píng)的解剖》中,指出歐洲1500年以來(lái)虛構(gòu)作品的重心一直在下移:先是羅曼史與出類拔萃的英雄作主角,其次是悲劇與具有權(quán)威與激情的主人公,再次是喜劇與普通人做主人公,最后是比普通人在能力和智力上低劣的人作主人公。由此,虛構(gòu)藝術(shù)進(jìn)入反諷時(shí)代,但在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(shuō)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種情形。羅曼史樣態(tài)的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(shuō)風(fēng)靡流行,想象和幻想力的發(fā)達(dá)是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(shuō)的一大特點(diǎn),且這一特點(diǎn)經(jīng)常通過(guò)某一非凡主角不同尋常的經(jīng)歷表現(xiàn)出來(lái),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大部分網(wǎng)絡(luò)小說(shuō)可以稱之為‘英雄’幻想小說(shuō)。”
這是什么原因呢?任何符號(hào)表意體裁終究會(huì)疲勞,終究會(huì)在似乎不可阻擋的“進(jìn)步”中變成反諷,又在反諷中耗盡自身,然后讓位給一種新的體裁,這種新的體裁又會(huì)開(kāi)始一個(gè)新的四體循環(huán)。人類的意義世界,就在這樣的表意方式循環(huán)中向前推進(jìn)。而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,目前受盡指責(zé)批評(píng),被看成輕薄為文,沒(méi)有深度,缺少品格,娛樂(lè)+商業(yè)。所有這些聽(tīng)了一耳朵的話頭,不就是17世紀(jì)小說(shuō)興起的時(shí)候受到的批評(píng)嗎?不也是一個(gè)世紀(jì)前中國(guó)晚清民初小說(shuō)大繁榮時(shí)的指責(zé)嗎?只要稍假以時(shí)日,歷史就看到了什么呢?同樣,要不了多少年,我們將也會(huì)看到新的文學(xué)的新經(jīng)典,迫使我們注視。
或有論者會(huì)說(shuō),我對(duì)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的這個(gè)定調(diào),是否太樂(lè)觀了?但是幾十年之后的讀者,也就是此刻在讀網(wǎng)絡(luò)文學(xué)的青少年成為社會(huì)中堅(jiān)時(shí),他們會(huì)覺(jué)得我對(duì)歷史還是太“鈍感”:明明一個(gè)嶄新的文化輪回正在開(kāi)始,而我還在欲吞欲吐,做種種保留,害怕直視歷史進(jìn)程的亮光。


